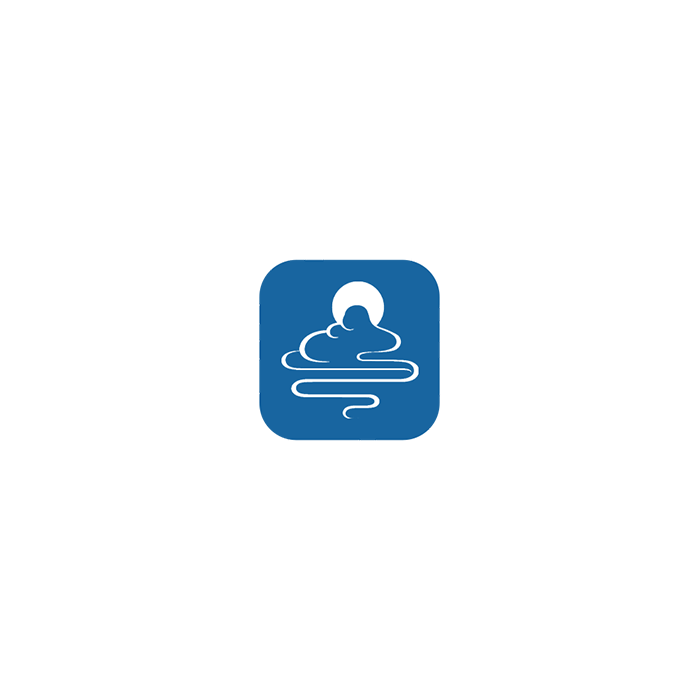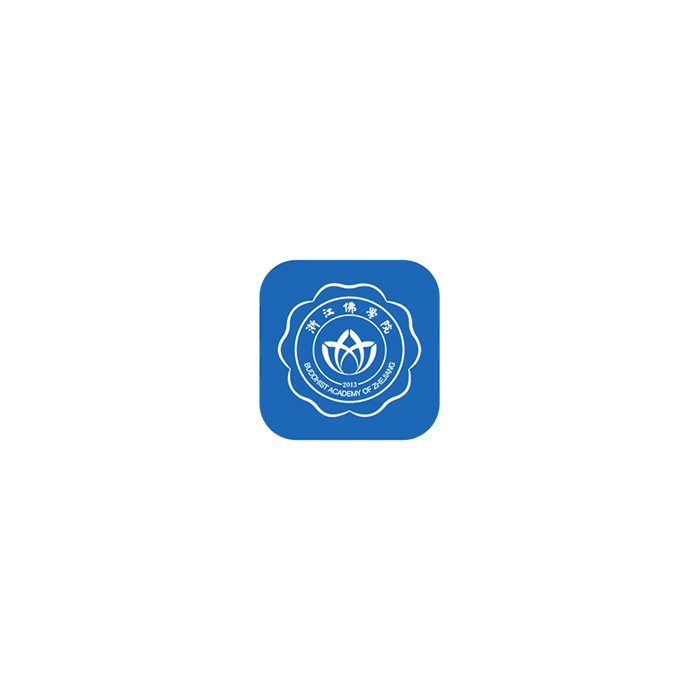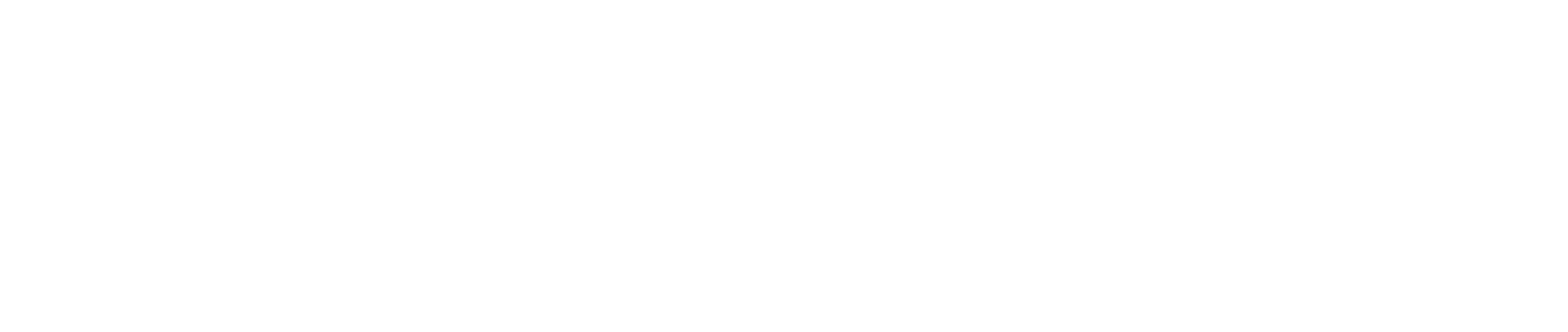
犍陀罗的弥勒信仰

来源:雪窦山

时间:2021.08.20

弥勒的变形:弥勒立像,拉合尔博物馆藏,出土于斯里巴哈劳尔大窣堵波。约公元2世纪前半叶。深灰片岩浮雕,高46厘米,宽17.5厘米,厚8厘米。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其波浪形的卷发和上身赤裸的肌肉造型,很有希腊艺术的风格。

皇兴五年(471)的弥勒造像,碑林博物馆藏
雪窦山的弥勒

中古时期弥勒信仰在中土的兴起
几乎每个宗教都包括了所谓的“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即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有受神派遣的救世主降临凡世,拯救一切人类和生灵,进入美好的时代。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救世主往往指弥勒,而非释迦牟尼佛本身。
“弥勒”,乃梵文Maitreya、巴利文Metteya的音译名;其它异译名尚有梅呾利耶、末怛唎耶、迷底屦、弥帝礼等。意译则称“慈氏”,盖其义为慈悲。
弥勒下生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标志是弥勒诸经的出现。竺法护在大安二年(303)译成《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此后,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四年(402)译成《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东晋时,有译者不详的《弥勒来时经》;北魏时则有菩提流支所译《弥勒菩萨所问经》等。根据这些经典,弥勒菩萨将在五十六亿万年后,继释迦而在此土成佛,仍然号“弥勒”,这即是所谓的“未来佛”或者“新佛”。根据这些佛经的描述,弥勒下生时,“阎浮提”世界会变得十分美好,人民康乐,没有灾难,“弥勒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
南北朝战乱频仍的环境下,对未来美好时代的期盼,给弥勒信仰的迅速普及和繁盛提供了条件。到了五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全部佛教造像中,30%以上为弥勒造像;北魏末至北齐、北周的四十年间,北方弥勒造像共88尊,其中仅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弥勒像35尊,占总数的近40% 。
佛教的飞翔之地: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兴起,佛像出现,佛经文本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菩萨理念的兴起
“菩萨”是犍陀罗佛教最为重要的创新概念,是其跟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区别之一。

菩萨的本意是“具备觉悟能力者”。觉悟之后的释迦太子称为“佛陀”,意思是“觉悟者”;菩萨则是未成佛但具备觉悟条件的人。菩萨可以成佛,但是他放弃或者推迟了涅槃,而留在世间帮助众生。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宣扬“佛果庄严,菩萨大行”,这跟“发出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旧传统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没有史料证明。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贵霜时期,菩萨在佛教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突出出来。菩萨的地位被抬高,随之而来的,菩萨像出现,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极为重要的表现主题和描述对象。
弥勒的犍陀罗源头
有的学者认为,弥勒就是阿逸多,也有学者认为弥勒和阿逸多是两个人。有的学者认为弥勒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位佛教高僧,是大乘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也有学者认为弥勒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有的学者将他和伊朗系神灵密特拉相连接,认为两者存在非常多共性(比如崇拜光明、发音接近等),在《薄伽梵歌》中,弥勒的名字是太阳神的名称之一。季羡林认为弥勒信仰跟中亚有关,“弥勒”是吐火罗语的音译。宫治昭认为弥勒信仰兴起和贵霜游牧民族对天的崇拜有关系,是佛教和游牧民族传统结合的产物;罗森菲尔德认为弥勒信仰跟印度的婆罗门教有关。尽管弥勒信仰兴起的历史背景和许多细节仍然如同迷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在其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1980年,今斯瓦特地区(乌苌国,Udyāna)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了乌苌国国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ā)于公元14年留下的犍陀罗语金卷,里面就提到了弥勒。
佛教在犍陀罗经过革新,飞跃进入中国,进而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菩萨信仰也沿着这样的轨迹进入东亚的信仰文化传统。弥勒信仰在贵霜时期兴起,进入东土,敦煌、云冈、长安、洛阳都广泛存在跟弥勒有关的图像。弥勒菩萨是犍陀罗菩萨信仰和造像最重要的主题,在原始印度佛教中,弥勒信仰并不发达。但在犍陀罗,数以百计的弥勒造像被保存至今。一般观点认为,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季羡林先生认为密教中弥勒菩萨处于西北方位,或许证明弥勒信仰跟西北印度关系密切。
《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弥勒大成佛经》都提到弥勒下生,世间“譬若香山”。所谓“香山”也就是犍陀罗。
弥勒交脚坐姿


一般认为,这种交脚倚坐弥勒像,表现的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的场景。有学者认为体现的是弥勒上生信仰——人们期望上生兜率天听弥勒讲法,但也有可能表现的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等待下生的场景。在巴米扬石窟有很多描绘交脚弥勒讲法的壁画,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入口上部中央半圆形地方,常常绘制弥勒讲法图。从绘画的方位来看,这体现的很可能是弥勒在兜率天的情形。
关于交脚倚坐的来源,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借用了贵霜王者的形象。季羡林先生认为,从中亚到中国新疆乃至直到内地的壁画、雕塑中的交脚弥勒,是受到了波斯的影响,古代波斯、中亚帝王和贵族就是这种坐姿。从贵霜王朝宫殿遗址哈尔恰扬(Khalchayan)出土的王侯像,君主就是交脚而坐。这是2世纪的情形。目前实物中最早的交脚坐姿是1世纪贵霜君主阎膏珍的钱币。似乎这种坐姿跟宗教信仰无关,而是俗人的坐姿。很可能由于弥勒信仰的流行,这种君主贵族的坐姿被用来描述弥勒。这种坐姿也许还跟游牧文化有关,西域坐胡床交椅的姿势就是如此。
弥勒交脚坐姿
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的金币,背面出现了佛陀的形象——佛陀被视为“神”是佛教很大的一个转变。

弥勒信仰的兴起应该跟贵霜帝国的政治宣传和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迦腻色迦铜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形象,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希腊字母铭文为“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虽然造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说明了至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仰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至少在迦腻色迦时代,弥勒作为未来佛的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

弥勒信仰的兴起应该跟贵霜帝国的政治宣传和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迦腻色迦铜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形象,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希腊字母铭文为“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虽然造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说明了至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仰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至少在迦腻色迦时代,弥勒作为未来佛的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
弥勒立像,塔克西拉博物馆

犍陀罗弥勒菩萨像一般带圆形头光,高鼻深目有髭,头发呈波浪形,头顶束发、结髻或戴敷巾冠饰,卷发披肩,佩戴璎珞、臂钏、腕钏等饰物,上袒下裙,具备了佛像的三十二相,例如头光、肉髻、白毫等。体现了弥勒既是菩萨,又是未来佛的双重属性。
七佛一菩萨
弥勒的三重身份(菩萨、未来佛、救世主),使得他在佛教宇宙观和时间观中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这一点反映最鲜明的图像是七佛一菩萨的构图。七佛信仰很早,在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佛陀耶舍和竺法念译《长阿含经》中都有记载。《魏书·释老志》对七佛的解释为:“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之。”
七佛的图像,早在公元前2世纪巴尔胡特的大窣堵波浮雕中已出现——用七棵树来比拟过去七佛。桑奇佛塔塔门浮雕中,也用七座窣堵波来象征过去七佛。
弥勒信仰兴起后,在犍陀罗地区跟七佛信仰相结合,发展出了“七佛一菩萨”的构图。目前犍陀罗浮雕中发现的此类图像,大多数是立像,少数是坐像。
多佛信仰在犍陀罗非常流行,常常看到类似“为供养过去一切诸佛”的发愿文,可以印证当时此类信仰被广为接受。宣扬多佛信仰的《佛名经》和《贤劫经》等佛经主张,通过念诵诸佛名号,可以洗刷罪恶、积累功德。此类观念在中亚非常流行,在巴米扬、于阗、敦煌均存在千佛壁画。犍陀罗窣堵波四周出现的多佛、千佛装饰,可能也是这种信仰的产物。

“七佛一菩萨”,白沙瓦博物馆藏
七佛和弥勒菩萨造像都雕造在长方形片岩饰物上。七佛在右,弥勒在最左边。弥勒菩萨肉髻赤足,右手上举肩侧,掌心向外,左手持“瓶”。七佛残一佛半,诸佛与弥勒皆有头光,但是手势略有差异,表现数是过去七佛的含义。

胁侍的弥勒菩萨,集美博物馆藏
北凉石塔

七佛一菩萨观念和造像传入中国,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米兰佛寺所在鄯善地区似乎流行这种造型。米兰佛寺出土了这一主题的多件木雕。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一件小乘佛教法藏部的佛教偈颂抄本,内容也是过去七佛的语录,说明这一地区曾经流行七佛一菩萨的观念。
酒泉、吐鲁番也曾出土多件这一主题的造像,比如北凉高善穆造石塔,覆钵下部一周刻拱形完,由七身佛陀和一身菩萨组成,和中土阴阳五行观念相匹配。弥勒菩萨头戴化佛冠饰,结转法轮印,交脚坐于方座上。坎卦(空间上位于北方, 时间上是一天最黑暗的夜半之时,一年的正冬之季),正与塔肩上的第七身释迦佛位于同一方位——表明现在是末法时代。
此外,云冈石窟也有七佛一菩萨的造像,有的铭文明确指出,是“造弥勒并七佛”。
弥勒大像

在犍陀罗大量发现的弥勒像说明了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弥勒下生信仰紧密关联的艺术创作是建造大佛。古代印度没有制造大佛像的传统,几乎看不到高达10米的大佛造像。目前已知弥勒大佛像是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建造的,时代是4世纪。
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弥勒大像建造于陀历国,是一尊木雕弥勒像。法显记载的“陀历国”,也就是玄奘笔下的“达丽罗川”(Darel,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大教宣流,始自此像”。弥勒诸经中提到,弥勒下生将以十六丈的姿容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在达丽罗山谷中,无法建造高达十六丈的弥勒像,所以从权减半,建造了八丈的弥勒像。在弥勒下生信仰中,八丈是个经常出现的敏感数字。弥勒诸经多次提到弥勒下生后,人的寿命达到八万四千岁,身长八丈,女人到了五百岁才出嫁。
从陀历往东,沿丝绸之路往东,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弥勒造像:巴米扬石窟(东边是高38米的释迦牟尼像,西边是高55米的弥勒佛像)、克孜尔石窟(第47、77等窟的大像,可惜今已不存)、敦煌莫高窟的北大佛(第96窟,高38米)和南大佛(第130窟,高26米)、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大佛、炳灵寺石窟大佛(第117窟,高27米)、天梯山石窟大佛(第13窟,高26米)、须弥山石窟大佛(高21.5米)、乐山凌云寺大佛(高71米)等。这些大佛基本可以判定是弥勒大佛,与弥勒下生信仰紧密相关。
弥勒大像的建造
武则天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僧人薛怀义等人谋划下,她宣扬自己是转轮王出世,在都城洛阳建造弥勒大像——象征弥勒下生。据文献记载,这座弥勒大佛身高百余尺。
弥勒大像的建造,甚至影响到日本,在奈良时期,日本也进行了跟王权关系密切的弥勒大像的建造。
7世纪以后,中土的弥勒巨像雕刻衰落了。弥勒崇拜逐渐从信仰的中心退却,其地位被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取代。

弥勒信仰和佛钵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佛钵东来是汉唐间中土的一个重要宗教政治预言。在犍陀罗造像中,弥勒经常和佛钵一起出现。图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浮雕。东晋兴宁三年(365),襄阳的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


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政府归还置放在喀布尔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曾引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下令将其运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塔利班当权时,很多佛教文物被毁,但这件器物因带有伊斯兰铭文而躲过浩劫。据汉文史料记载,佛钵是在公元2世纪上半期,被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从毘舍离(Vaiśālī)或华氏城(Pāṭaliputra)抢到贵霜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ṣapura,即弗楼沙)的。这也是现在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的“历史依据”。佛钵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
犍陀罗的弥勒像经常出现佛钵的符号。

大都会博物馆藏弥勒立像

集美博物馆藏
艾娜克出土的 “燃灯佛授记” 浮雕,镀金彩绘,高41厘米,宽25厘米,时代大约属于3—5世纪。完整地表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教理念。而且在台座上,用佛钵象征了弥勒成佛(未来)。三世佛的理念已经非常成熟,和云冈石窟表现的思想如出一辙。值得指出的是,表现过去和表现未来的场景中,出现的故事、符号,都是犍陀罗本地的历史记忆。


艾娜克遗址


佛钵保存在白沙瓦地区;燃灯佛授记故事发生在贾拉拉巴德地区;造像出土于艾娜克地区,相去不远。

迦必试出土的造像(集美博物馆藏)和艾娜克出土造像的对比——其表达的宗教思想是一样的。


燃灯佛授记非常重要,它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是佛传故事的开端。它发生在犍陀罗。

燃灯佛授记与弥勒信仰的关系:历史学的观察
弥勒授记也是从燃灯佛授记接续的,过去已经成功的授记,为弥勒授记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燃灯佛授记奠定了释迦牟尼成佛的理论基础;对应的,释迦牟尼为弥勒授记,奠定弥勒将在成佛的神圣性。
中国佛教将燃灯佛、释迦牟尼、弥勒视为三世佛。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燃灯佛授记和弥勒授记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准确对应。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燃灯佛授记,为弥勒信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感想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一个最初的佛教。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这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按照这样的逻辑,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西方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其实,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
犍陀罗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中国中古史、中国佛教史和汉唐间的美术史。以历史学的视角,综合图像、文献、考古、宗教等研究方法,才能让有关犍陀罗的历史信息焕发出生命力。
即便是研究中国文明本身,我们也许仍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国境之内。古代文明从未不是完全割裂和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至少一个区域的)人类文明视为整体,从各种狭隘的羁绊(民族、国家、宗教认同等)中拯救历史。(文/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